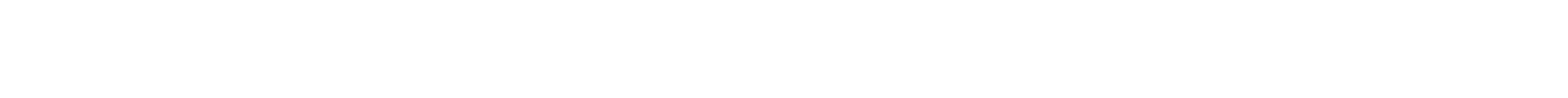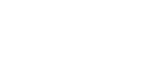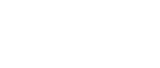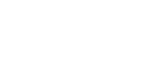文学欣赏|杨方 风吹木扎尔特(二)
| 招商动态 |2017-07-03
风吹木扎尔特(二)
麦维蓝眼睛里开始有了不为人知的忧伤。那时候麦维蓝还没有来月经,但是麦维红已经在两年前就来了,她在麦维蓝面前极力表现出一个成熟女人的样子,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穿毛料的方格子长裙,弹琴的时候还要特意裹上麦妈深灰色的羊毛大披肩。因为是冬天,麦维红改成在壁炉前弹奏卡龙琴,壁炉里燃烧的松木劈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房间里无处不在地弥漫着一股松木死去的淡淡的味道。跳动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着麦维红的脸。麦妈对这样的情景很是满意,有时候她会忘记时间,长久注视着麦维红,仿佛坐在那里弹奏的是她自己。麦妈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从上海来支边,邂逅了同样从遥远莫斯科来支援中国建设的年轻医生,友谊医院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友谊医院旁边的绿洲广场,每天晚饭后成了苏联专家活动的场所,他们在那里拉手风琴,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那时候中国人会跳交谊舞的几乎没有,挤进去凑热闹的是些大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们天生酷爱跳舞,听见音乐就身不由己,哪管节拍和舞步是否协调,交谊舞的曲子,配上他们晃动脖子抖动肩膀的新疆舞蹈买西来普,那种滑稽的结合,引得围观的人大笑不止,一场舞会被搅得不伦不类。中方领导认为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严重到有可能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于是紧急派出医院的年轻姑娘学跳交谊舞,以便每个苏联专家都能有一个舞伴。那时候麦妈在兵团农四师医院当护士,因为来自洋气的大上海,自然也在医院派出的人之中。她的舞伴是年轻医生,两个人除了一曲接一曲忘情地跳舞,还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在杨树成排的深夜的斯大林街散步。后来风云突变,两国关系紧张,苏联专家们一夜之间撤走,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接下来的几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各自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苏漫长的边界,几乎成为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女知青在一片打倒苏修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暗自伤心了将近十年才缓过神来。她遇到孪生姐妹的父亲的时候,他刚以一个排长的身份从部队转业,被任命为天西林业局下面一个林场的场长,并分得了一套苏联专家留下的房子。女知青正是因为这座苏联风格的房子和麦场长结婚的。在想象里,她是和那个莫斯科的年轻医生,按苏联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无情的现实却是,她不得不忽略那个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麦场长,曾经的麦排长,是对苏战斗的英雄,著名的塔斯提事件发生时,正是这个排长带领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赶到并开火还击。当时在牧区放牧的支边女知青无端被苏军开枪打死,在附近巡逻的麦排长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拔枪还击,因此立功,也因此受到批评,提早转业。
教麦维红弹琴的是伊犁河边看苹果园的一个叫法拉比的老人。在女知青被思念和绝望苦苦煎熬的那些年的一个春天,苹果花开得铺天盖地,这个承受着爱情离别却又无处倾诉的女知青,独自跑到伊犁河边望着流向苏联的河水无限哀伤地坐了一下午,返回的时候,女知青路过一座苹果园,听见有人在繁花深处唱歌,歌声悲怆,像清亮的雪水冲下帕米尔高原,又像茫茫戈壁的烈日下孤独行走的人突破重压发出的呐喊。
女知青沿着苹果园的土围墙走了大半圈,找到一个用沙枣木阻挡的缺口,她小心地避开木头上长长的尖刺,钻了进去。接下来她在飘洒着冰凉花瓣的苹果园里跌跌撞撞地走了许久,时而迷路,时而驻足倾听,歌声始终清清楚楚地缠绕在大团的白色花朵间,似乎就在离她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唱歌的人,她感觉到自己正被某种奇异的魔力所控制,忍不住想要放声痛哭一场,就在她想要找到缺口出去的时候,却一转身看见了一群衣衫灰暗的人,围坐在一棵树冠如云的苹果树下唱歌,他们用力地跺着地上的尘土和落花,歌声起伏,合声呼应。盘腿坐在中间弹奏卡龙琴的清瘦老人,正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木卡姆歌手法拉比。他指下碎裂般的琴声苹果花一样纷飞,坠落。
法拉比老人当时年岁已经很大,有人说他七十多岁,有人说解放前他就已经七十多岁了。给麦维红教琴的时候法拉比老人看上去依旧是七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清瘦,头戴黑色丝绒绣花小帽,旧靴子外面永远穿着一双黑色套鞋,进门的时候,他把套鞋脱在门边,显得极其礼貌。他来的时候也永远是乘坐马车而来,那是一辆铺着红毯子的马车,蓝色天鹅绒的顶棚边缘挂着黄色流苏,马笼头上悬着装饰物,但是没有铃铛。这样的马车那时候已经不多,因为不被允许在大街上出现,只能在小胡同里或城市的边缘行走,偶尔捎一两个搭车的人,马蹄哒哒,不慌不忙。
尽管麦维蓝和麦维红已经不再那么相像,法拉比老人还是不停地把她们混淆。他要求麦维蓝端正地坐在卡龙琴前,纠正她的指法,节拍,音阶和调式。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练习了很多年卡龙琴的演奏者,在每一首曲子的演奏中都错误百出,手忙脚乱。麦维蓝恨自己不是蜈蚣,有用不完的左手和右手。
“胡大诶,你一定是生病了。”老人有时候会怜悯地摇着他的头。
孪生姐妹又一次玩起了互换身份的游戏。这让她们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的亲密无间。她们为毫不费力地骗过老人而偷乐。一段时间以后,麦维蓝已经能和麦维红弹得一样好,甚至在某些难度较高的地方,比麦维红领悟得更准确。在夏天接近尾声,苹果快要成熟的时候,法拉比老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果园,他要赶走跳进围墙偷果子的调皮巴郎,要捡拾被风吹落的果子,用小刀把它们削皮,切成片,晾晒成苹果干。孪生姐妹于是商量,两个人轮流去果园弹琴。
第一天,麦维蓝弹奏了《纳瓦木卡姆》第三达斯坦的第一乐段,她把V级音2升高了四分之一音,结束的时候以7为结音。第二天麦维红也弹奏了同样的乐段,法拉比老人指出她弹奏得和昨天不一样。昨天的弹奏法是民间的,野性的,也是挥霍的,接近南疆刀郎木卡姆的味道,今天则是华丽的哈密宫廷木卡姆风格。孪生姐妹觉得,老人并非弄不清谁才是他真正的学生,他极有可能是故意混淆她们的。木卡姆面临失传的危险,老一辈知晓整套十二木卡姆音乐的人,除了法拉比老人自己,别的已相继凋零,每年春天,再没有人围坐在开花的苹果树下大声地弹琴唱歌。那些宝贵的传统音乐,正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知道木卡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弹奏或唱。人们对木卡姆的遗忘让法拉比老人忧心忡忡,多一个人学唱,也是好的吧,更何况麦维蓝对木卡姆有着如此惊人的天赋。
等麦妈明白过来自己被一对孪生姐妹所愚弄的时候,这种游戏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她看着她们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很是恼火,觉得如果不把这两个人分开,后果不堪设想,真不知道以后她们还会弄出什么离奇的事情来。也许谈恋爱的时候她们会假扮成对方轮流去约会也说不定。麦维红已经矫正了牙齿,麦维蓝发育之后反而瘦下来,两个人留起了一样长的头发,穿着一样的裙子,再次变得十分相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麦妈去木扎尔特送麦维蓝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上学,这三年麦维蓝按麦妈的意愿在一所学校专门学习俄语。一整个学期,她都得待在学校里,虽然学校离家并不远,但麦妈不怎么允许她回家,更不允许孪生姐妹和希林有过多的来往。其实希林那时候已经调往木扎尔特海关当翻译,他除工作之外整天还要忙于各种各样的翻译,帮某个公司谈一批钢材的价格,给新开张的大酒店签一份旅游合同,有时候是帮浙江老板把服装批发给奇缺物品的乌克兰商人。那些年木扎尔特经常可以看见的一幅景象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国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体型大于他三倍不止的穿着暴露的俄罗斯女人,她一半裸露在外的乳房足有篮球那么大。希林穿着海关服,即便是在大街上行走,也随时会被这样的陌生女人拉去当翻译,买化妆品,买糖果,买丝袜,买吊带衫,买红茶,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他们都会毫不选择地买了带走。有时候大街几乎成了自由市场,堆满了山一样的货物,有人手里一边数着卢布,一边在五色杂陈的货物间奋力地挤来挤去。
唯一保持安静的是最初的木扎尔特存留下来的五座老房子,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竟然没有把它们拆掉。也许人们根本犯不着费那力气,四周多的是空地,曾经麦穗起伏的大片麦田也早已荒芜,再没有人会撅着屁股在烈日下的田间辛苦地劳作。他们随便圈一块地就可以大张旗鼓地盖房子,开店铺,然后一夜之间把身份从农民转换成商人。这一切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全国进行着,因为信息的畅通,木扎尔特在这一次的变革中也不曾落下步伐,当地政府努力地让这片荒寂的地方充满时代的气息,邮电局,卫生所,餐馆,酒店,车站,银行先后出现,最显眼的是海关,那座崭新的海关大楼就建在老房子的前面,每天,巨大的玻璃幕墙闪耀着蓝色冰块一样的火焰,投射在五座已经不再有人进出的老房子上。麦维蓝想起十四岁的那个夜晚,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打麦场,五座老房子像是漂浮在水中,新麦草在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香泽。
她不敢相信短短的几年木扎尔特就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正是这一年,中哈两国政府同意口岸向第三国开放,木扎尔特因此具有了国际联运的地位。有着狗鼻子一样灵敏嗅觉的南方商人,在伊犁州政府卖力的招商引资下,以淘金者的冒险心态争相涌入,他们带来沿海浓重的商业气息和难懂的方言,把木扎尔特这个地图上无人问津的小圆点变成了集商贸,购物,旅游为一体的繁华城镇,每天大批货物在这里中转,国际邮件在这里进行交换,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关进出,一切呈现出任何时代也无法企及的喧闹和繁荣。就算是在大汉或盛唐,这里也仅仅是商队的歇息地,过往的商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连绵的帐篷中,烧茶的炊烟一股一股升起,金色夕阳照着成堆的茶叶和布匹,然而第二天商队过后,除了一两家孤独的客栈和遍地的马粪骆驼粪留下来,一切重又恢复远古的荒寂。如果是在清朝,中俄两国不时发生战争,这里更多的是狼烟四起的景象,清政府在界河边立下的一块石头就是最好的说明,青灰色大石的一面刻着士兵们英勇杀敌的经历,另一面则刻着清朝历代皇帝多次对他们嘉奖的事迹。如今宽宽的界河不知道在何年代就已干枯,除了尸体一样遍布的石头,整条河床干燥得简直能冒出烟来。听说两国政府正计划在这个地方合作铺设一条铁路,他们的宏伟计划是将木扎尔特这枚弹丸之地发展成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那时候,谁又能想象得出这里会是一副怎么样的景象呢?
遥远时空的再现,现在的日新月异,将来的不可预知,在麦维蓝的脑子里交替出现,她无法弄清一个地方几度兴起到衰败,是否每一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这个词,在木扎尔特是三维立体的,它包含过去的重现,现在的穿插,未来的颠倒,也包括自己此时短暂的停顿。这一刻,亚细亚的群山正笼罩在金黄的阳光下,麦维蓝看着将要去的远方,无法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到过去,还是为了去往未来。她觉得不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是在世界的原地打转。
当麦妈看着麦维蓝跨过国界线,穿过一片尘土弥漫的空地,走向邻国长途汽车站的时候,她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苏联人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闪亮的手表朝这边使劲挥舞,许诺只要一过去,就可以领到一块手表。很多人涌到边境,徘徊,犹豫,叹息,流泪。最终有少数人迈出了脚步,他们脸上是赴死般悲壮的表情。当年那个被爱情燃烧的女知青也想跟着他们过去,她在国界线这边站了一个星期,最后哭着鼻子返回了伊宁。
这一次麦妈在边境停留了大半天,希林带她走遍了每一条街道,在俄罗斯人的商铺里麦妈买了许多小东西,城堡式样的牙签筒,镶着假珠宝的首饰盒,沉重的金属小圆镜,还有俄罗斯红肠,大马哈熏鱼。中午他们在一家维吾尔餐馆吃拉条子和烤肉的时候遇见了羊毛胡同马忠义的老婆,这个头戴纱巾的回族胖邻居在木扎尔特租了店铺,经营胡椒粉,咖喱粉,孜然粉等各种调料。麦妈和胖邻居热切地聊了一中午,请她喝了正宗的俄罗斯噶瓦斯酒,最后麦妈听信了这个颇有商业头脑的胖邻居的建议,她们在饭后一起去看了那个计划中的火车站,并决定在火车站旁边买下一块地皮,将来盖起两层楼的店铺,光租金算一算就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虽然眼下所谓的火车站还是一块荒地,遍布石头和苦豆草,其间只有几头驴在那里悲苦地啃着草皮子。但据胖邻居说,勘测人员已经来过好几次,她亲眼看见过他们画出的草图,图纸上火车站出口的方位正是驴经常打滚而草皮裸露的那个地方,旁边是一个现代化的广场,有花圃,还有喷泉和大理石柱,广场旁边就是计划中的商铺。可想而知,那些商铺的生意该有多好,买了那里的地皮就等于买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麦妈对胖邻居的话深信不疑,回到羊毛胡同之后立刻打
 招商热线:400-151-2002
招商热线:400-151-2002